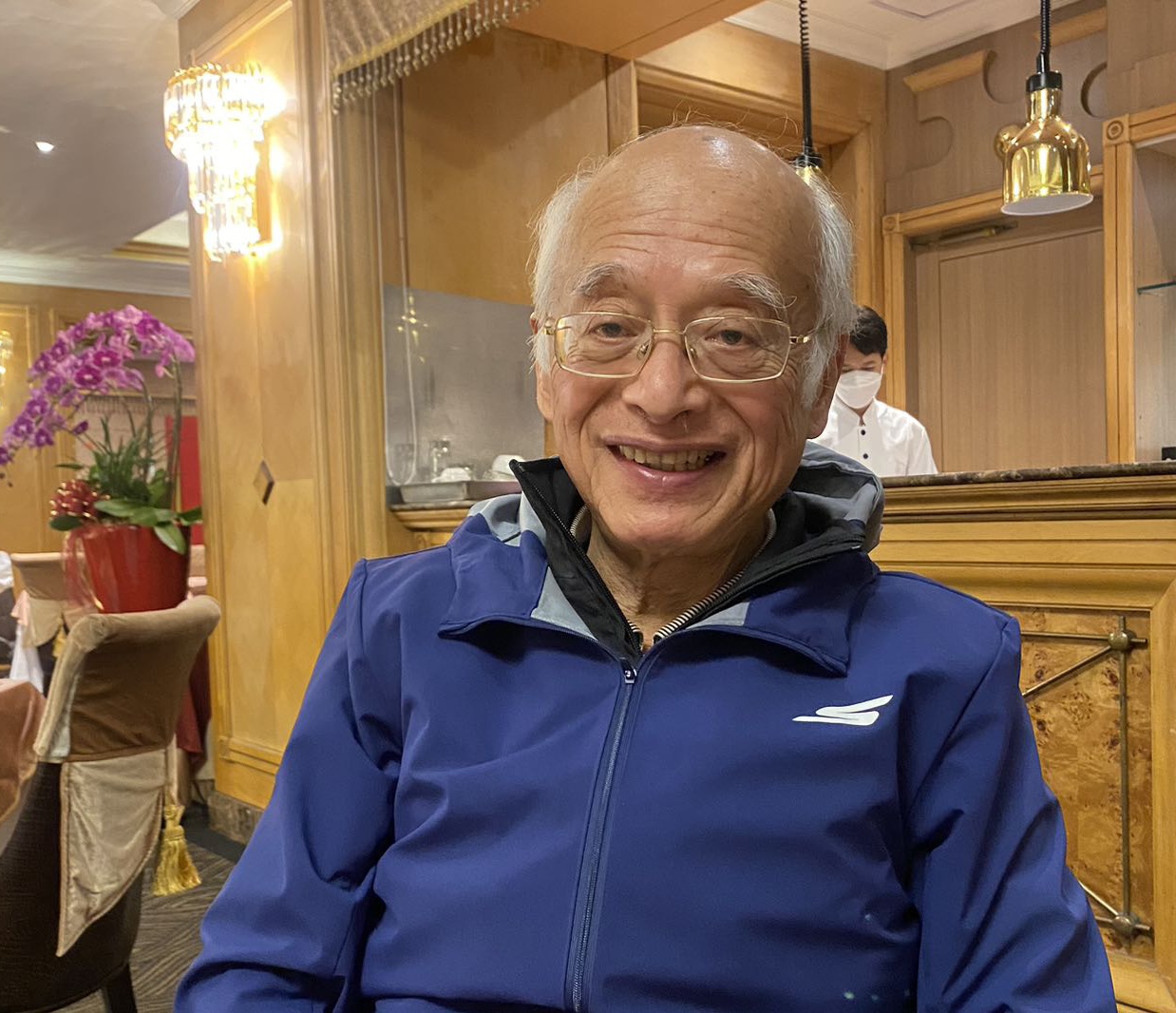知中疑美:拯救台灣的中道 紀念胡佛與朱雲漢教授—黃光國

知中疑美:拯救台灣的中道
紀念胡佛與朱雲漢教授—黃光國
元宵節過後,立即傳來兩件噩耗:首先是九十七歲的星雲大師辭世,接著是六十七歲的朱雲漢院士病故;前者令人感到不捨,後者使我覺得震驚:一九六七年,我返回台灣大學心理學系任教,曾經到法學院兼課,朱雲漢曾經修過我教的社會心理學。當年上課時,他喜歡針對重要問題,追問不捨的情況猶歷歷在目,怎麼會這麼快就走了?
胡佛的志業
朱雲漢是胡佛教授的高足。胡佛(1929-2018)是江蘇揚州人,父親戴天球曾加入中華革命黨,追隨孫中山,參加革命。抗戰勝利後,獲選為第一屆制憲國大代表。胡佛從母姓,故改姓胡。
胡佛青年時其跟大多數華人知識份子一樣,深受「五四意識形態」的影響,篤信「民主」與「科學」是可以「救中國」的兩尊「洋菩薩」。1949年五月,胡佛隨父親從上海乘船抵台,考入台大政治系。畢業服完兵役後一年,即申請到美國愛莫瑞大學(Emory University)獎學金,主修「美國政府」與「美國憲法」。獲得碩士學位後,返回台大政治系任教,即以「推動民主憲政」作為終身志業。
那時候,正是台灣黨外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,1975年,在《聯合報》發行人王惕吾的支持下,《中國論壇》成為當時學院派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重要的輿論陣地,胡教授參與筆陣,他跟楊選堂及韋政通三人,是讓這個陣地發揮巨大能量的三位靈魂人物。此外他還在報紙雜誌上,寫出數百篇政論,鼓吹民主憲政,並且和楊國樞、張忠棟、李鴻禧等人致力於黨內外溝通,成為社會公認的「四君子」,國民黨內則稱之為「四大寇」。
1979年十二月,美麗島事件爆發,胡佛等人不顧自身安危,多方奔走,營救因該事件而被收押之嫌犯,最後終於獲得總統蔣經國約見,而使美麗島事件能大事化小。
「論政而不參政」的「中道」
1986年九月,民主進步黨成立,在胡教授和陶百川等中介人士的折衝與協調下,歷經艱辛,終於化解了朝野衝突、零和對峙的危機。
民進黨成立後,朝野對立情況日趨嚴重。1989年四月,楊國樞與胡佛等人倡議效法英國「費邊社」,號召學界及社會菁英,共同組成「澄社」,胡教授身為關鍵發起人,並親自撰寫成立宣言,原本期望社員處在朝野之間,可以發揮「論政而不參政」的「中道」精神;不料事與願違,「澄社」成立後不久,內部發生「憲政體制」爭議,胡教授堅持主張「內閣制」,但遭到強力反對。他察覺到「澄社」可能變質為「渾社」,當年十二月,即協同創社成員文崇一、韋政通、何懷碩退出「澄社」。
楊國樞教授是位十分重感情的人。當我發現「澄社」已經背離「論政而不參政的原則」,我也不再參與「澄社」活動。後來有一次,我問楊先生:為什麼還不退出「澄社」?他一臉苦笑,搖搖頭說:「嗐!畢竟是自己一手創立的社團……,」到了扁政府時代,許多「澄社」成員紛紛出任政務官,「澄社」也背離了創設時的理想,淪為「政務官養成所」。
在大是大非的選擇方面,胡教授的作風就果決得多。1994年,李登輝在國民黨內開始掌握實權。三年後的六月,邀請胡教授以「憲法學者」的身份,參加國是會議的預備作業。當他察覺李總統的修憲意圖,竟然是推動台獨分裂,動搖國家認同,從根本上違背憲政主義與自由民主的精神,立即斷然退會,拒絕為掌權者背書。當年六月24日,他更帶領「台大關心憲改聯盟」十多位教授。赴陽明山中山樓,遞交台大校務會議的修憲建言,及校內近二千名師生聯署「反對修憲謀權」的名冊,提出抗議,並要求停止修憲。
在兩岸關係方面,胡教授生前最擔心的是對於政治人物因為認同錯亂,或政治計算,刻意製造台灣兩千三百萬人與對岸十四億人之間的疏離、敵意與對立,他認為:這樣的操作手法,既不負責任,也極不道德。
「佛門弟子」
胡佛反對台獨,1980年代中期,他更邀集同道,組織「中流文教基金會」,劍及履及,的推動兩岸學者的交流與合作,但他從來不干預他人或學生的政治信仰,也不認為參加民進黨就必然會主張台獨。
他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堅持是「科學研究方法」。從1980年代,他便帶領研究生,在台灣開始從事政治文化、政治態度、以及政治參與的實徵研究。那時候,我在台大心理系開設「多項變數分析」統計課程,他特別要求他指導的研究生游盈隆和陳明通前來選修。1997年,他在幾位研究生的協助下,將自己在這方面的研究和著述,整理成《政治學科學研究》立本專書出版,從〈方法與理論〉,談到〈憲政結構與政府體制〉。
他認為:大學必須在自由與自主的環境中,才能充分實踐學術上的尊重理性與開放,因此,他旗幟鮮明的主張:「在台大校園中,不接受任何不容批評與詰難的學說與意識形態,也不允許任何政治勢力滲入校園,干涉我們自主的學統。我們的學統只有學術權威而無政治霸權」。他所帶領的研究生也因而自稱「佛門弟子」。
「統一是必要之善」
很多人覺得奇怪:像胡佛這樣的自由主義大師,為什麼會主張國家主義?2013,他以〈國家統一是必要之善〉為題,接受《觀察》月刊的專訪。他很清楚地表明:
國家層次的自由,是指一個國家不能受到他國的控制與干涉;否則這個國家就不能自主、不得自由。真正的自由主義者除了重視政府與個人之間的個人「小我」自由,更應重視國家的「大我」自由,因為如果國家遇到內亂、外患,不能凝聚、自主,就失去了自主運作的自由,必無法保障國民的個人自由及社會的安寧。如此看來,國家的自由可稱為「大自由」,是大我透過國家這個政治團體行駛的集體自由;人民的個人自由則是「小自由」,只是針對國家統治機構的政府而言的,要求政府權力不要限縮個人自由。從政治體系看,「大自由」與「小自由」不在同一層次,「小自由」必須有「大自由」保障,兩者並不互斥。
記者進一步問他:「為什麼台灣會有這麼嚴重的國家認同問題?」他很精闢的分析:
過去日本人先有計畫地用皇民化教育來抹去認同中國的道德感情。日本人走後,兩蔣又基於國共內戰之需,一方面為醜化中共而連帶傷及對整體中國的感情,一方面又不惜引入外力(從整體中國立場來看),出讓了局部的大自由(國家主權)給美國。現在,則美、日還想繼續控制台灣,將其歷史觀、價值觀灌輸給台灣,並藉台灣干涉中國內政。台灣唯美國人馬首是瞻,有形無形都受控於美國,等於是變相的殖民地,根本沒什麼大自由;而在民粹炒作之下小自由又如此混亂。
穩定政權的治理能力
從2001年起,他帶領「佛門弟子」,開始從事「亞洲民主動態調查」,朱雲漢教授是這項研究計畫的主持人,也是他最重要的得力助手。2007牟之後,這個研究擴展到東亞14個國家與地區,探討公民政治和行為的變遷。五四時期,中國知識分子普遍認為:「民主」是可以救中國的兩尊洋菩薩之一,但是長期實徵研究的結果卻一再顯示:中國大陸民眾對其政治體制的滿意度和支持度都相當高。這個穩定的現象迫使他們必須深入探究其中緣由。
這個問題跟日裔美籍政治學者法蘭西斯·福山(Francis Fukuyama)的理論轉向十分類似。1990年代,前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崩解之後,他出版了一本名著,叫《歷史的終結》(The End of History)(Fukuyama,1992),認為:二戰後東、西二元對立的冷戰局勢,已經走到了歷史的終結,從此之後,全世界都將走向資本主義體制。
可是,他很快地就發現:這種主張跟世界發展的方向並不相符,2014,他出版一本題為《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》的書,修改他的理論,認為穩定政權的治理能力取決於三項要件:(1)強大的現代化國家;(2)依法治國;(3)政府問責的能力,能夠使人民產生信心。
高思在雲
朱教授不僅研究東亞國家的政治體制,他對西方「自由主義」的異化,也有很精闢的見解。冷戰時期,西方國家為了對抗共產主義的擴張,大多施行夾雜著社會福利政策的「鑲嵌式自由主義」(imbedded liberalism)。1980年代之後,美國雷根總統和英國柴契爾夫人大力推行「新自由主義」(neo-liberalism),卻使西方世界逐步陷入危機。而美國「國防/軍工/國會」三合一的複合體是導致其政治衰敗的主要緣由。2015年,他出版「高思在雲:一個知識分子對於二十一世紀的反思」,很坦誠地說出他的見解。
在該書中,朱教授也探討:「民主為何讓台灣民眾失望」。他指出:「變形民主耗損台灣治理品質」,「政黨利益糾葛延宕社會發展」,「媒體是政治損耗的重要推手」,「台灣是富豪的樂土」,同時希望大家能夠反省:「台灣距離民主崩壞還有多遠」?
為了確保自己論述的正確性,朱教授利用他「中央研究院院士」和「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」的雙重身分,不斷地和國際政治學者交流意見,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,並出版論文集《西方中心世界的式微與全球新秩序的興起》,其中文譯本於2020年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。
中共的「體制摸索」
然而,他的觀點卻得罪了政治立場不同的當權派。2021年,和他同為中研院院士的朱敬一出版了一本書《維尼、跳虎與台灣民主》,直接點名批判朱雲漢,說他常發表極端歌頌中國共產黨的言論,「非常嚴重的誤導讀者」。朱雲漢2012年在台灣大學的一場演講中,認為中共的經濟成長模式在美國是資本主義和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(福利國家)之外,開創出了第三條道路。「他會逼著第三世界所有國家的政治菁英重新去思考,怎麼樣去平衡正當程式、維持國家治理能力、取得最好發展結果」,朱雲漢認為,中國經濟的崛起得益於中國的政治體制。
「中國共產黨這個體制摸索奮鬥三十年,這三十年並沒有白費。很多人以為中國一九四九年到改革開放,三十年都浪費掉了,是完全黑暗時期。這個認知本身就是錯誤的……反而可以說,中國這個時期以高昂的社會代價—很多人因此而犧牲—去建構了改革開放的基礎,這個基礎讓其他國家沒有辦法去模仿……另外,中國完成了一場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,因為他把私有財產權,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資本集體化,不是國有就是集體所有。而這個龐大的集體資產,大部分是國有資產,是中國後來三十年快速發展的資本。」(頁184)
這個論點,引發了朱敬一的高度不滿。他說: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這三十年間所推動的土改、鬥爭、人民公社、三面紅旗、大躍進、土法煉鋼、文化大革命,加總起來人民死亡至少六千萬人。以大躍進為例,毛澤東要求農民「密插秧」,聲言「膽量有多大,產量有多大」,逼著各地只好謊報生產數字。中央以謊報數字抽糧稅,於是人民剩下來的糧食不足,卻又在高壓體制下不敢言語,乃造成四千萬人活活餓死。這種天怒人怨的暴政,就是朱雲漢口中的「體制摸索奮鬥」?(頁185)
為中共「擦脂抹粉」
因此,他認為:朱雲漢的說法是為中共「擦脂抹粉」、「論述蒼白且錯誤百出」、「明白悖離人本精神」,「豈止是令人遺憾」!
乍看之下,朱敬一的批判似乎有其道理。因為「四人幫」在1976年垮台之後,中共自己也否定他們在這段期間的作為,並且把四人幫的垮台以及後來的「改革開放」,稱作「撥亂反正」。
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,一個社會由「亂」而求「治」,最後走上「正」軌,這就是一種「體制摸索」的過程。朱雲漢說:「中國這個時期以高昂的社會代價—很多人因此而犧牲—去建構了改革開放的基礎」,是根據他多年研究心得所做出的結論。在朱雲漢看來,朱敬一書中痛斥的那些「文革亂象」,正是中國所付出的「高昂代價」,所以他特別強調:「很多人因此而犧牲」。
從這樣的析論來看,他們兩人對於這個議題,其實各有立場:朱雲漢的立場是「知中」。他站在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立場,對於自己所研究的對象,要有「同情的理解」,並且要求他自己以客觀中立的語氣,論述他的研究發現。朱敬一的立場則是「反共」,站在「啟蒙運動以來數百年的人文精神」,堅決反對「共產極權」。在2020年台灣由民進黨主政的政治氛圍下,一位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新書發表會上,公然批評另一位院士「親中」,這等於是戴他一頂「紅帽子」。我原本以為朱雲漢會出面辯駁,但是他沒有。他選擇沈默。
「台灣必須覺醒」!
最近兩岸關係愈來愈緊張,很多人擔心:在美國不斷「加柴添火」的情況下,兩岸隨時可能擦槍走火。新北市長候友宜主張:「不當強國的棋子」,執政黨主席賴清德立即回應:不可以讓「疑美論」成為社會共識。2023年元月13日出版的「天下雜誌」,朱雲漢抱病發表了一篇的文章,題為《美國軍售地雷,台灣必須覺醒》,警告國人:
邪惡的美國鷹派,打算把台灣的剩餘戰略利用價值,透支到極限。把台灣蹂躪成為廢墟後,北京即使拿下也只剩沉重包袱,至於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是否將陷入絕境,將失去戰後七十年的現代化建設成果,美國毫不在乎。
在美國政府威逼下,台積電將最先進的三奈米半導體生產線設置在亞利桑那州,並陸續釋出最核心的技術。美國強迫我們恢復義務役、準備打巷戰,近期一‧八億美元軍售案,都可看出這種戰略思維。
五天後,馬上有另一位「院士級」的台大敎授公開出面叫陣,說「疑美論」如果占上風,將會「弱化台灣防衛」,「使台灣走向敗亡」!言猶在耳,事隔不到一個月,竟然傳來朱敎授英年早逝的消息!這時我才深刻體會到:他以「中研院院士」和「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」的雙重身分,發表這些言論,需要多大的智慧和勇氣!
朱雲漢逝世後,我仔細回想:他以清冷的批判意識倡議「知中疑美」,其實傳承了胡佛教授當年創立「澄社」時的「中道」理想。胡教授生前經常對老友慨嘆:在「民粹主義」盛行的台灣,學術界講究的是「西瓜偎大邊」,所以「中道」很難找到市場。然而我卻認為:他們師生二位窮其一生之力所提倡的「知中疑美」,正是拯救台灣的不二良方。有識之士,請三復斯言!